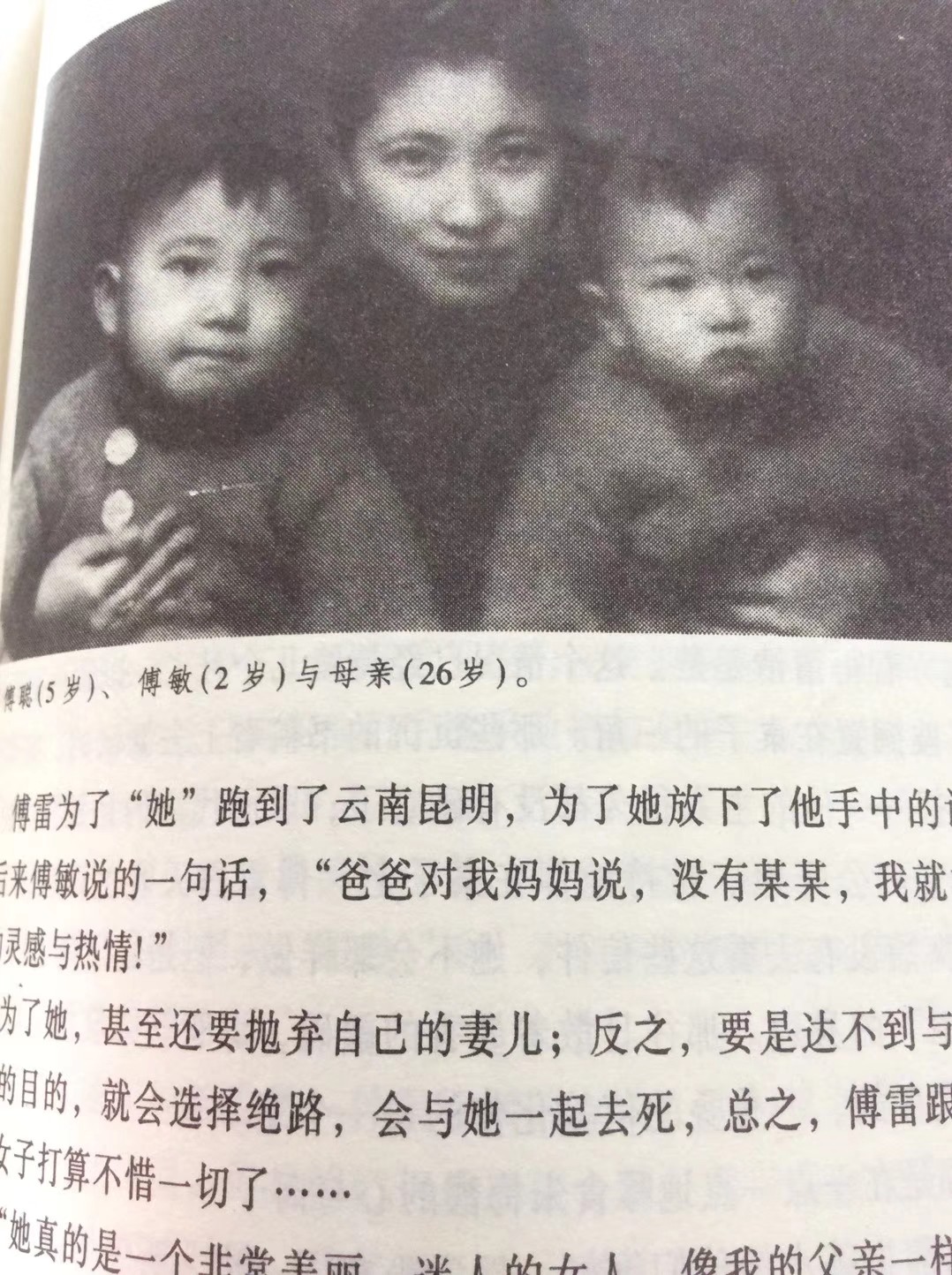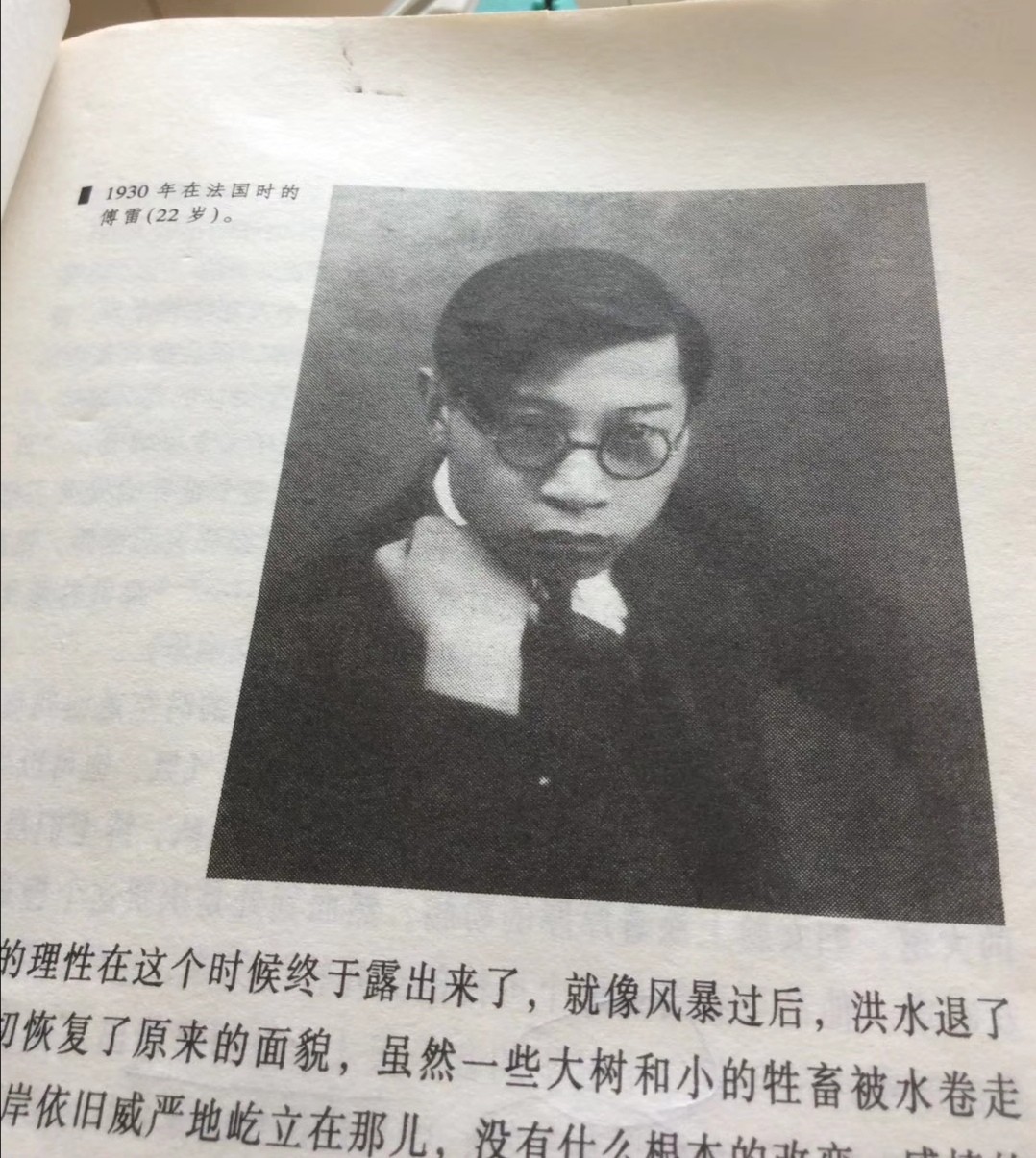这次疫情,上海医生张文宏出名了,不过最近却被一些人骂,说他非常有钱,还杜撰了他的“惊人”收入。这不由得让我想起前几年袁隆平的遭遇。
袁隆平有一次一下买了两部华为手机,还有一次车展他上手摸了一下豪车,这就不得了了,那些极左的人便认为:正面的英雄,劳模,伟人,他们就应像雷锋一样事事谨小慎微,不能吃好饭不能穿新衣,他们就应是永远的苦行僧般生活者。如果他们象正常人有七情六欲那就不得了了,炸开了锅。
这种极左年代错误地灌输养成的固化意识:穷人才是好人,好人一定都是穷人,穷人变富就是腐败,就可恨可恶。这种人表现往往是:见穷人他们笑或者欺,见富人他们恨或者骂,他们只有一个愿望:就是回到过去,渴望火烧火燎的革命场面,这样他们流氓的才能便能发挥得淋漓尽致,过足了人瘾。
古人云:取之有道,也就是靠劳动,靠智慧致富,那是人间正道。
每个人不仅是羡慕,更应学习,只当全社会普遍建立起这样一种积极致富,而不是仇富嫉富损富,或想着法子劫富济贫这样一种价值观,那么这个社会便会逞现出一派有力出力,有智出智,有钱出钱蓬勃向上的创富观,界定,理顺这种人人该有正当劳动产品的所有制关系,于是便能做到:各尽所能,按劳所获,大家都无怨言。同时又能帮助:失劳供养,供其所需。社会便无仇恨。
总之,所有这些实现的前提必须是:劳动必须个人能够获利,如此便才有持续不竭的劳动原动力,社会财富才可能高涨,它产生的结果是:主观为自己,客观却为了社会。
说白了,社会财富要持续增长,就是要不断地调整所有制,即个人,集体,国家三者分配的比例是否合理?不然就会挫伤人这个个体的劳动积极性,从而使整个社会财富增长减慢。
现在有些人又在鼓动:一大二公,兴无灭私,你我不分,大哄大上大锅饭,什么共同富裕,其结果是奖懒罚勤,滋生懒汉,偷尖耍滑,不仅共同富裕不可能,连个体富裕都泡汤。
所谓公平竞争是必须的,但公平分配则是极其错误的,永远也不可能,因为若没有差别就没有动力。
来自于 [WhereIn Android] (http://www.wherein.io)
This page is synchronized from the post: ‘奇怪的逻辑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