白也诗无敌,飘然思不群。
清新庾开府,俊逸鲍参军。
渭北春天树,江东日暮云。
何时一尊酒,重与细论文。
——杜甫《春日忆李白》
读到“远上寒山石径斜,白云生处有人家。停车坐爱枫林晚,霜叶红于二月花”,有的小朋友就会自动把“斜”字读作“xiá”。再比如李商隐“晚晴风过竹,深夜月当花。石乱知泉咽,苔荒任径斜”,如果读“xié”就真的太不和xié了。
这其实是一种权宜之计。汉语语音大体可以分为上古音,以《诗》为代表;魏晋以来转变为中古音,唐诗宋词便是;元以后形成近代音,就和现在的普通话比较接近了。唐诗宋词既然用中古音写就,其韵部、声调和个别字的发音与现代汉语自然会有不小的差别。东南沿海某些方言保留了一定的中古语音成分,因此念诗时偶尔会感觉到比普通话更协调。
但方言也不尽然是古语,里面同样有大量当地土话、外来语言篡入,全都混在一起,要还原诗词的本音依然非常困难。如果不是这些地区的人,要学会方言更不容易。
诗词声律的本意是使人读着流畅又有变化,即是所谓的“抑扬顿挫”,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构成感情表达的一部分。所以一般来说,我们没有必要完全返回中古音,只要能读得感觉好就足够了。
什么程度才称得上“感觉好”呢?也许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要求。
我的基本要求是:押韵、平仄协调、整体和谐。
用普通话读《春日忆李白》,就会发现每一点都有可商榷的地方。
押韵:群、军、云……文?前三个字在普通话里的韵母都是un,偏偏文是en。然而,在唐代发音里,他们的韵母是相同的。
一般写诗时我们用《平水韵》作为参考。《平水韵》其实不是唐人的作品,而是宋代后期平水人刘渊,根据当时通行的韵书,结合唐诗的押韵情况整理得来。不过好在唐宋韵书不少,从《切韵》、《韵镜》到《广韵》、《集韵》,有着系统、可靠的源流资料,所以中古音谬误、争议不是特别多。
古代诗人写诗并不翻什么韵书,自己念念对得上就行了。然而诗人有时代、有方言、甚至有自己念错的字,韵书无法考虑这些。单本韵书也很难反应随时代变迁发生的语音转变。这一点是我们在读诗词,尤其是魏晋诗、明清诗词,参考《平水韵》时心里应该有所意识的。
回到“文”字来,《平水韵》里属于阴平第十二个韵部,通常叫做“十二文”。这个韵部里包含了云、文、分、薰、斤、昕。好吧,un、en、in俱全,还有我们现代汉语的第一声和第二声。而在唐宋时,它们的韵母、声调是一样的。
考虑到情况如此复杂,对于这种问题,我的建议一般是……如果方言里有的话,可以用方言带一下;没有的话,就不用管它了。
再说平仄协调。
按照《平水韵》,“白也诗无敌,飘然思不群”是仄仄平平仄,平平平仄平。一般遇到这种情况,古人会把“思”读作“sì”,于是仄仄平平仄,平平仄仄平,就是完美的仄起不入韵式首联。
如果按照普通话来读,则变成平仄平平仄,平平平仄平。咦?还是大体合律的。这就是我们用普通话读起来也并不觉得很别扭的原因。
可是“月出惊山鸟,时鸣春涧中”就大不一样。连用“月”、“出”两个入声字,这一联出句其实是非常逼仄、狭迫的。月光忽然明亮起来,才有“惊”,才能和对句“时鸣春涧中”的舒缓幽然形成对比。用普通话读则一整联都是平静的,韵味不足矣。
平仄的问题多是入声字引起的,普通话和很多方言里没有入声。我一般建议先读这个字的轻声,然后把它缩短、加重。
最后一句“重与细论文”里,论字该怎么读?
大家都知道《论语》是读平声(包括第一声和第二声),其它还有读平声的吗?其实古代“论”字读平声稍多,仄声也用。两种读音在意义上没有明显的差别。现代汉语以为平声多做名词,仄声多做动词,古代则并不如此。
我隐约觉得有些多音字其实并不完全是为了区分词性、意义,有些根本就是变个声调读起来流畅,后来也就成了定式。
在这一句里,古人多读平声,也就是“重与细lún文”。
这是由于两个原因:一,观察细、参、暮、论,正是仄、平、仄、平。二,“何时一尊酒,重与细论文”按律应该是平平平仄仄,仄仄仄平平。
这些其实无谓,关键是自己多读几遍。觉得平声有味道,就读平声;如果感觉仄声更合适,就读仄声。
这首诗还有拗救的问题,暂且不说了。
This page is synchronized from the post: 【读杜诗说】(6)春日忆李白|月旦评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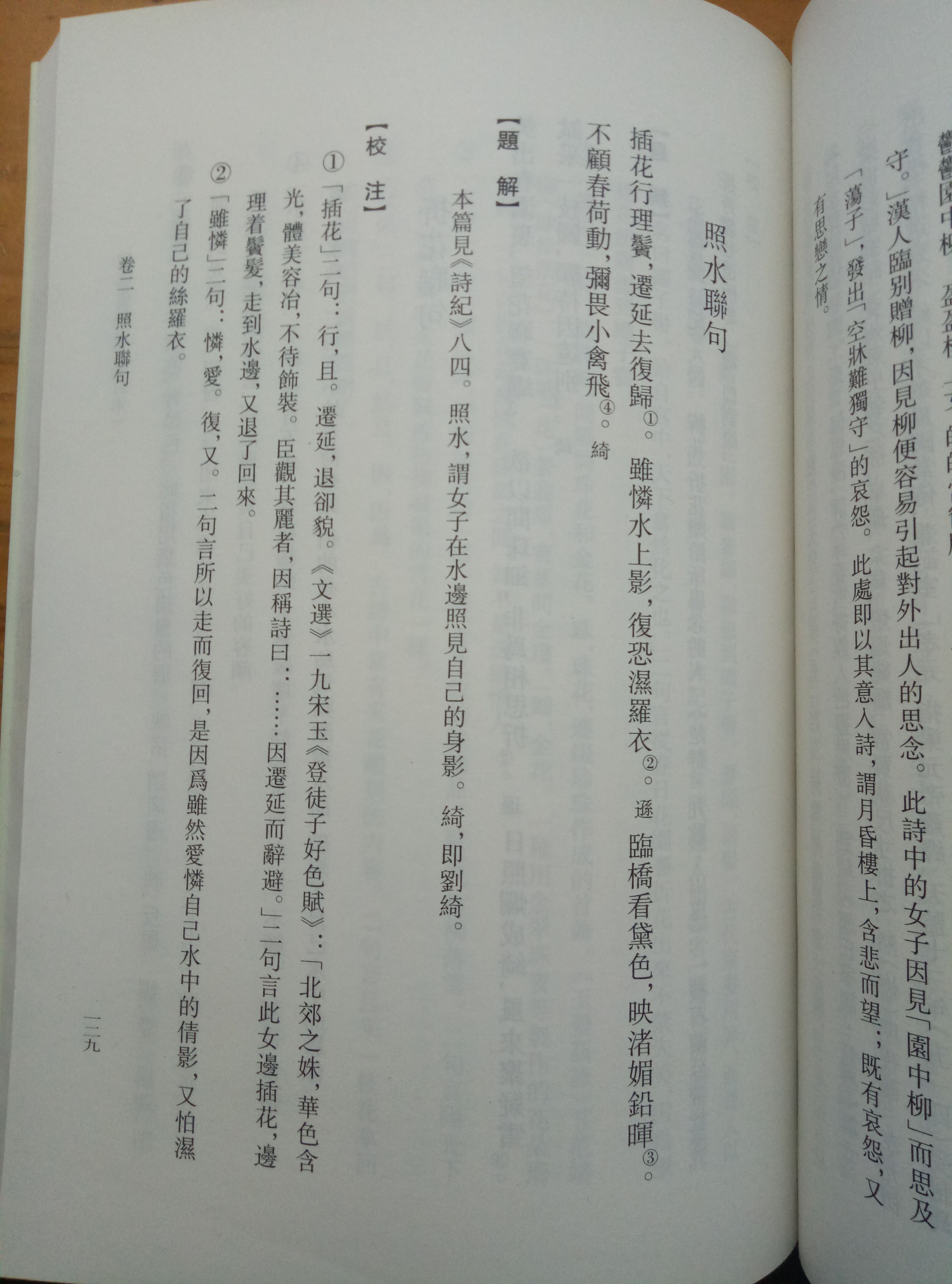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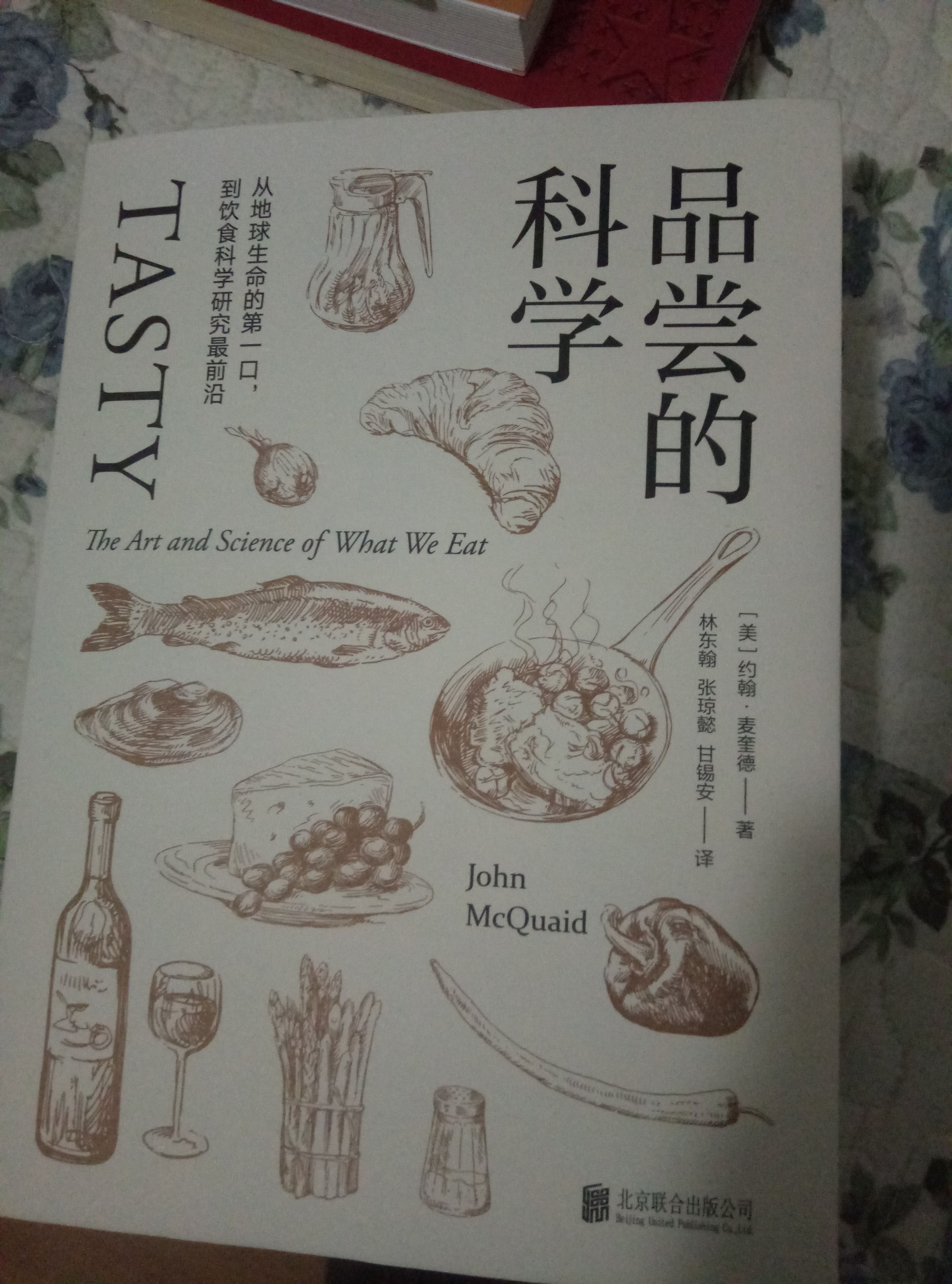.jpg)
